佛教艺术的兴起正值孔雀王朝,当时印度正与波斯、希腊进行文化交流。为了传播佛教,阿育王下令开凿洞窟,建造舍利塔。桑吉大佛塔的门雕、婀娜多姿的药师佛、鹿苑的狮子柱头、帕鲁德围栏的浮雕,几乎是早期印度佛教雕塑的精髓。波斯艺术的装饰图形、希腊艺术中对人体性特征的表达,都可从中找到传播的基因。
贵霜王朝时期(公元1至3世纪),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与印度北部的马图拉是贵霜王朝的两大雕塑中心。此外,在安得拉王朝统治下的印度南部的阿马拉瓦蒂,佛教雕塑自成一派,与犍陀罗、马图拉平起平坐,成为这一时期的三大艺术中心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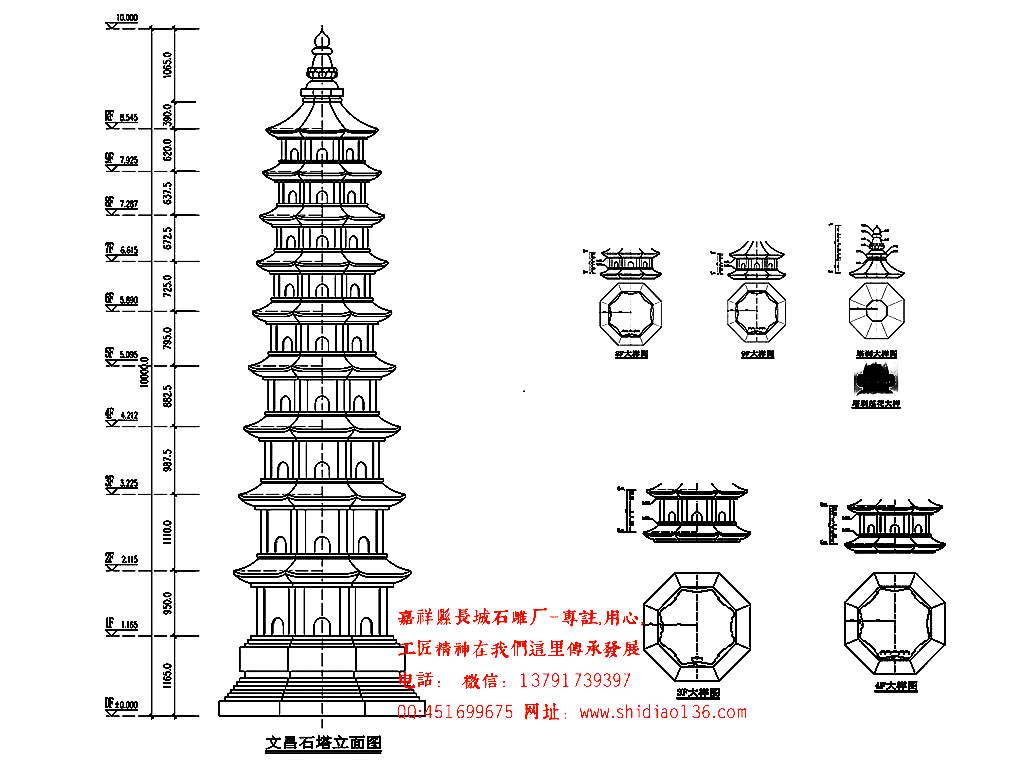
犍陀罗的创始人最初是公元1世纪进入此地的月氏人(敦煌附近),后来扩大了疆土,定都于巴基斯坦白沙瓦。此地曾长期被希腊人占领,留下了希腊式的雕刻艺术。犍陀罗人吸收了古埃及、希腊、罗马、波斯的雕刻手法,并加以发展,形成了表现优美的比例、和谐的几何形状、真实而富有生命力的人体雕刻艺术。佛像顶部的肉髻上披着希腊雕刻中常见的优美自然的波浪卷发。佛像披着齐肩的袈裟,类似希腊、罗马雕刻中的长袍,褶皱厚重。面部表情朴素、高贵、沉稳,半闭的双眼透露出沉思、内省的神情。

马图拉艺术强调健壮华丽的裸体之美和力量感。佛像身穿露出右肩的薄而透明的外衣。犍陀罗的波浪卷发已被剃发所取代。
犍陀罗雕塑艺术影响极为深远,主要传播到西北、东北和东南地区。3世纪以后,向西传播到阿富汗东部和中部地区。著名的巴米扬石窟被认为是晚期犍陀罗艺术的代表作。印度佛教艺术的西进只到达中亚部分地区,在巴米扬停止后又折返传播到远东。

东北有一枝沿着丝绸之路进入新疆和中国内陆。佛教艺术向中国内陆的渗透,沿着云冈、龙门、响堂山三条路线发展。云冈的巨佛造像,直接从岩石上凿刻而成,这种手法完全是印度的。衣纹的螺旋纹与巴米扬的佛像一致,又有犍陀罗风格的硬朗。但到了河南龙门石窟,中国艺术家已经能充分吸收印度和中亚的风格。龙门石窟与云冈石窟的区别,是造像更具东方色彩。响堂山石窟则是另一种鲜明的形式:柱状人物像表现出建筑的性格,并加入了一些珍贵的珠饰。这三种类型的进一步融合,发展出了大唐风格。唐代以后,大唐风格从中国流向高丽和日本。 高丽时期许多重要的寺庙和佛像,如须须寺、宗圣寺等,在韩国文献中都说是由唐朝派来的“中国工匠”完成的。佛像雕刻也受到“六朝风格”和“隋唐制度”的影响。日本最重要的寺庙是奈良的法隆寺,建于公元610年左右。这座世界上最古老的木造佛寺,完全按照中国六朝时期的寺庙规模修建而成。法隆寺的木造佛像至今仍是日本最精美的佛像,佛像的火焰形衣饰虽具有六朝特征,但仍不失犍陀罗的韵味。金殿(佛殿)四壁的净土化身图和四大天王是韩国人在公元712年绘制的,其风格与印度著名的阿津天壁画十分相似。 在东南方,犍陀罗艺术与印度北部的马图拉雕塑并行发展,成为印度笈多王朝佛教艺术的先驱。

笈多王朝(约公元320—535年)被誉为印度艺术的黄金时代。笈多式和萨拉那特式佛像是由贵霜王朝的犍陀罗佛像和早期的马图拉佛像演变而来的。其特点是:佛像的卷发改为戴宝帽,腰身由粗变细,眼睑下垂,表现出平和静谧的气氛。衣服由宽松变为合身,由多层变为单层,衣服的褶皱变为月牙状,富有韵律美。笈多式佛像伴随着佛教的传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东南亚、中亚、中国、朝鲜和日本等地的佛教造型艺术,甚至比犍陀罗佛像的影响更为深远。
斯里兰卡与印度相邻,佛教文化艺术一直是斯里兰卡的主流,尤其是佛教雕塑艺术,受印度的影响最大。色克利耶岩上岩画中的散花女神,是真正的笈多时期阿旃陀风格。阿努拉德普勒的晚期佛像,双手结禅定印,衣服褶皱清晰,也接近笈多时期萨拉纳特风格的佛像,十分精美。斯里兰卡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从那里的港口可以很快通向缅甸、泰国,这两个国家和斯里兰卡一样,也是小乘佛教国家。目前发现的众多雕塑、青铜器造型以及主要佛像的薄而透明的衣饰,都显示出它们与印度笈多王朝晚期风格的渊源和关系。

笈多时期以后,佛教在印度逐渐衰落,逐渐被印度教同化,演变为密宗佛教。在古印度另一边的孟加拉国,佛教艺术中渗入了大量印度教元素。佛教密宗的雕塑打破了笈多时期的古典艺术规范,佛像风格高度程式化,动作、姿态夸张,讲究更为繁复、扑朔迷离的“手印”,纹饰精致繁复,大量使用尖拱、火焰等图案。孟加拉的这一风格,形成了笈多风格艺术和尼泊尔、西藏艺术向密宗佛教的过渡阶段,其中又以藏传佛教艺术影响最大,成为佛教艺术的晚期形式。
从印度的阿旃陀、阿富汗的巴米扬,到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柬埔寨的吴哥窟,再到中国的克孜尔、柏孜克里克、敦煌、炳灵寺、云冈、龙门,再向东流向朝鲜、日本,这些佛教艺术瑰宝犹如一串串璀璨的宝石,散布在亚洲大陆,散发着艺术的光芒,记录着人类交流的历史,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您可以选择一种方式赞助本站
赏